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达伦·阿斯莫格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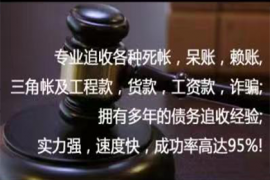
背负着超过7.5万亿美元外部债务的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着日益沉重的偿债成本,而这一切又恰逢它们需要尽可能扩大财政空间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之时。尽管有充分理由去减免大部分债务,但许多主要参与者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将限制这些国家未来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进而压抑投资和增长。
但支撑上述观点的证据其实相当薄弱。国际金融流非但没能可靠地促进投资和增长,反而更可能助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动荡。即使如此,学术界和政策界长期以来依然假设这些国际融资可以帮助新兴经济体建立更有效的体制,比如协助它们发展自身银行体系和股票市场。同时那些反对债务减免的人还指出,新兴市场需要国际债券市场所施加的“纪律”,因为资本外逃的威胁会让独裁者和民粹主义者有所忌惮,不敢乱来。
因此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各方都尽力劝阻希腊人对外国银行债务实施违约,以免损害其信用记录。虽然希腊选民拒绝了三大官方债权人(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条件,但该国的左翼政府最终还是珠海要账公司达成了协议,这让许多政策制定者得出了市场纪律有用的结论。
但是这种说法已经不再正确。国际融资非但没能管束独裁者,相反还一直在为他们提供便利。比如2009~2018年间的南非,尽管时任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的专制政府显然正在掏空该国的经济和体制,外国资金却依然不断涌入。而祖马的最终倒台只是因为他所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罢免了他,与国际市场的监管关系不大。
同样,尽管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对其国家体制的破坏伴随着该国投资和生产率增长的下滑,但外国投资者却拉了他一把。不断流入的资金为土耳其日益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提供了资金,同时也支撑了步履蹒跚的经济,使得埃尔多安得以巩固自身统治,甚至打造了让议会和法院听命于他的总统制。与祖玛一样,埃尔多安面临的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国际市场,而是国内政治,在去年的市政府选举中他的政党在大部分主要城市中败北,致使其权力遭到极大削弱。
除了这些例子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国际融资其实公然助长了新兴市场中的腐败和犯罪活动,例如高盛集团就涉嫌参与了马来西亚案值7亿美元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欺诈丑闻。这些事件其实都不足为奇,试问国际金融机构凭什么不去抓住机会向独裁者发放高息贷款,或者通过帮助窃国者和不诚实企业做假账和利用避税天堂来增加自身利润?
为了跨越这种破败的现状,我珠海讨债公司们应该寻求一些可以斩断腐败政权的债务重组和减免形式。有个想法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机构来为国际性银行的公平借贷行为制定规则,还可以由该机构来确定一个国家的当前债务是否是在民主政府统治下积累的,是否是盗窃和欺诈性借款的遗毒,以及这些债务的偿还是否会给该地民众带来不必要的苦难。
对于那些在民主政府统治下借款的国家,可以以慷慨的方式重组外债,还可以向长期债权人和在新兴世界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人提供类似的选项(因为这些形式的贷款不太可能会落入独裁者的腰包)。对于第二类国家,应该注销过去由独裁或腐败政府积累的“恶意债务”,因为普通民众不应为那些金融机构与未非由他们选出的政客之间达成的交易承担后果,而那些与窃国者签订浮士德式交易的投资者则不应受到国际保护。
至于第三类国家——社会无法承受其偿债成本的政府——则显然不应强迫其陷入更深度的贫困,即使它们的债务是由民选政府造成的。那种认定大规模债务重组和减免意味着新兴市场无法获得充裕资本的假设并无充分依据。即便这些国家拒绝进行重组或减免,这些债务负担仍将遏制其对基础设施,扶贫和新技术的进一步投资。
同样重要的是,免除恶意债务将改善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的激励因素,致使放贷人不得不在支持专制和腐败政权之前三思。这一转变可以为设计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一体化框架提供动力。
不过这种手段只有在免于对国际金融进行全面否定的情况下才会起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用于投资和基础设施的资源,也依然可以利用大量负责任且受监管的国际金融流。我珠海讨账公司们决不能造成一种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获得任何融资的状况。
为此,应明确规定债务重组和注销是一项紧急措施,而且该措施会将那些正规机构和与腐败和专制政府打交道的机构区别对待。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不仅要监督未来金融活动的规则和监测金融不法行为,而且要支持新的全球规范和标准框架。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确保该体系在发展中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眼中的合法性。